◎ 宋 扬
《庄子·在宥》说:“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土从大地上站起来,立而为墙,土地只是完成了一次外形上的物理改变。墙体是土,房顶是土中长出的毛竹、蓑草、稻草或麦秸杆。水归其壑,土返其宅,某一天,土墙倒下去,在风中,在雨中软烂为泥,又以物理的方式与大地合二为一,浑然一体。这是一个原始而自然的闭环。
石灰石和粘土合体,高温是火热的婚床,催生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水泥;铁矿石在烈火中淬炼,化为钢铁,铁骨铮铮。就本质而言,钢筋水泥依然是土地的孩子,却早已离经叛道。钢筋水泥带着仅存的丝丝毫毫土地的质性逃离大地,向高处一米一米延伸,可与天公比高。钢筋水泥撑起的摩天大厦与它们脚下的土地,像极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与母亲——那是粘合不到一起的磁铁的同极。孩子们一个接一个逃离,土地痛惜,十年或二十年,那些土做的墙还将认祖归宗,以土的身份回归土地怀抱。一百年、一千年以后,土地如何才能融软那些钢筋水泥冰冷坚硬的心!
《周易·象传》写到:“地势坤,土地厚德载物。”土地既生长鲜花遍野,也接纳人类制造的一切垃圾——干的,湿的,能回收的,不能回收的,可降解的,不可降解的。土地隐忍,鲜花摇曳,它不笑;垃圾遍地,它不怨。论土地对垃圾的消解力,僻远荒村完胜繁华市区。叶落一片,在农村,无人在意;在闹市,竟成环卫工人的宿敌。落红带情,纷纷入地,在土里,化作护花春泥;在柏油路,车轮碾过,雨一下,它们只能淌成一地散发腐朽气息的烂泥,让走在上面的人们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土地与日月星辰相照望,上纳风雷雨雪,下养虎豹虫蚁。土地滋养植物、动物。植物以落叶、以枯枝、以零落成泥的消失滋养土地,动物以粪便、以骨肉分解重归土地。土地出产粮食、蔬菜、瓜果供人类食用;土地出产树木、钢筋、水泥供人类使用。人类将废弃物全部抛还土地。钢筋水泥如何反哺土地?土地与人类曾双向滋养,投桃报李。而今,似乎只剩人类对土地的单边掠取。人类制造的生活垃圾即便采用焚化、堆肥、分选回收等方法进行处理,也总有一些剩余物,需要采用以土填埋的方式进行最后处理。人类觉得土地有肚量,肆无忌惮。土地隐忍包容的极限确乎没有穷尽?土地是我们的遮羞布,土地替我们藏污纳垢。布被撑破之时,科幻小说家星新一作品《喂,出来!》中的那些被人类制造并被倒入大地深洞的垃圾会不会井喷如雨?
行道树下,土地被压缩到只剩二尺见方的块状或直径不过一米的环形。土地之外,混凝土从四方挤压过来。包围圈严丝合缝,钳制有力,像如来佛之五指一样,时刻宣示自己对那些桀骜不驯的树之永恒控制力。方寸土逼仄,雨稍小,树喝不饱水,得依赖环卫工人定期浇水维持生命。当新铺设的柏油路,以每小时上百米的速度扑过来的时候,蚯蚓、蚂蚁、蛇鼠们反方向逃离的脚步,能否快过滚烫的沥青和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压路机?一个城市,如果只会统计人均占有多少住房面积,占有多少公共资源,享有多少医患比……无人关心,大都市动辄上百平方公里的水泥地下,有多少沉重的呼吸急促奔向那一小块一小块裸露的土地。声音在一棵棵树下汇聚,喷涌,叫人想起夏日池塘的水面上,缺氧的鱼儿朝向天空的嘴巴。嘴,密密麻麻。人,不寒而栗。
在我每天上班的路上,一群鸟儿定时从头顶的天空高高飞过。不远处,是城市新修的湿地公园。公园的存在,大概算是一座城市对土地最后的尊重。显然,这不是一群外来的鸟类,丛林里的鸟不会舍本逐末,来城市定居。也许,它们是这里的土著。如今,它们也已流离失所。鸟儿如我——一个远离了村庄的“都市人”,隔断了同土地血脉相连的脐带,也成了固无居所无处安放身体与灵魂的漂泊者;鸟儿如我,鲜明地感受着远离土地后生命异化的惶惑与萎顿。鸟儿并不知道自己可以迁去哪里,抑或,它们在等待树木、田园、河流、生命一个一个次第重回土地。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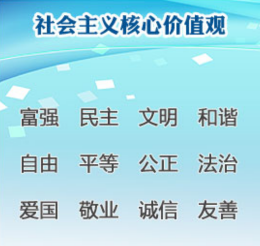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