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友洪
我的老家有一眼极其普通毫不起眼的老井,但它却是我们的宝贝,全家人身上都流淌着老井的血液。今天,我就来讲讲老井的故事。
我的老家紧邻大凉山麓,那里是四川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尽管那里山高水长,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了诸多不便,比如我童年时候的饮水,就是个问题。
老家的房屋建在一片坡地上。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刚出生时,我的父辈们在那坡地上平了块台地,在上面立了房子。之所以在那坡地上立房子,是因为那坡脚下,有一眼泉水,终年不枯。那个年代,择屋基首先得解决水源问题。于是父亲决定,房子就建那里。
那个地方叫垮山。
房子建好了,父亲就开始修水井。靠土坎的一边是泉水淌出的地方,得留着,其余三面则用石头垒砌,还用泥巴塞满石缝。老井一经使用,就从未偷过懒,曾经有几次大旱,老家其它井都枯了,唯独老井的水还不知疲倦地冒着,乡亲们就到我家来分水吃。
老井是朴实和无私的。它毫不吝啬地捧出自己清冽的甘泉,不求半点回报。老井似山里人的性格,也如我的父母。
老井不大,仅半米见方,盛满水能挑三五担。我的老家吃水全是靠挑的。我十一二岁开始,每天早上的第一堂功课就是挑水,之后才摸着发痛的肩膀出门去上学。不是父母不疼爱我,那时还没实行土地承包,父亲在一矿上做工,母亲一大早要出门去挣工分。农村孩子有的是力气,挑水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这个排行老大的身上。
我的父母育有四个男孩。在那个以工分糊口的年代,要养活四张嘴巴,谈何容易!弟弟们穿的衣服,大都是捡哥哥穿过的,因此那衣服常常让母亲在煤油灯下补了又补。我们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到井台上去洗,老井似乎也发出了无声的叹息。我是老大,自然没有哥哥衣服可捡,只好穿父亲在矿上的劳动服,乡亲们都戏称我长大后是“打煤炭”的。如果逢年过节能添件新衣,哪怕买双新袜,我们就很满足了。
其实我们这点苦,比起父母的艰辛来,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的父母为这个家孜孜不倦,默默奉献,倾情付出。父亲到一个煤矿做工,母亲就在生产队挣工分。由于我家人口多但劳动力少,每年都是“倒差户”,生产队年终分完粮食,父亲得拿上挣的大部分钱,去补给生产队。
那时我的父亲在矿上过得十分艰苦。父亲不识字,只能做些井下的粗活、重活,当然工资也很低。父亲省吃俭用,最大限度地把钱节约下来拿回家。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矿上几乎没吃过一顿肉,很多时候是就着从家里带去的咸菜吃点“汤泡饭”。父亲很爱我们,他每次回家没钱给我们买零食,就用饭票给我们换矿上食堂的馒头,又白又大的那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饭量也越来越大,生产队分的那点粮食远远不够吃,父亲就拼命工作,多挣钱买高价粮。有一次加班,父亲因疲劳过度,头晕导致受伤,右脚小腿骨折了。还有一次,煤井垮方,父亲躲避不及,把自己埋在了坑道里,肋骨被打断了三根,万幸的是捡回了一条命。父亲在煤矿上干了二十多年,受过三次伤,有两次差点连命都丢了。父亲为了我们,无怨无悔。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母亲每天一大早就在生产队长的吆喝声中出工了,妇女那时被称为“半劳动”,劳动一天的工分只相当于“全劳动”(男人)的三分之二。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只要有机会,她总是争着去干“全劳动”做的活儿。遇上计件的活,母亲就不停歇地做。母亲有胃病,就是那时饱一顿饿一顿落下的。
实行改革开放土地承包,日子才迎来了转机。那是在1983年,我家第一次不用买高价粮或者借粮食吃也能度过青黄不接的六月了。后来,家里开始有了余粮,能喂年猪了。再后来,家里有了余钱,有了存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父母将那土屋换成了砖混结构的小楼房。此时我们再到井台上去挑水洗衣,看着老井,都觉得它在为我家生活的改变而开心地笑呢。
真正彻底解决吃水问题,是在本世纪初。国家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投入了大量资金。我的老家就是用管道,把大面沟的溪水引到垮山,再修水池进行过滤、沉淀,然后通到每家每户。现在只要一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哗哗地流。
自此,老家挑水吃的历史就结束了。
如今,我的父母依然把那口老井留着。由于不常使用,老井的井沿上已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井壁上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草覆盖着,更显其沧桑与朴素。
我懂得父母的心思——这口已经五十多年的老井,见证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记录着一户普通的山村农家的苦与甜。
(作者单位:四川省眉山市政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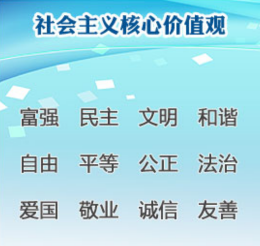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