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测
翻开我珍藏已久的影集,扉页相片是一位身着军装、英姿勃勃的妙龄女郎。她姓田名媛,是一位大学生。田媛既不是军人,又没参加过军训,甚至连民兵都没有当过,她那身军装从何而来呢?我迷惑不解,似乎又有些明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崇尚军人,尤其是年轻姑娘们,把找个军人做丈夫当成第一选择。即便找不到军人做丈夫,能穿一身军装,或者与军人站到一起照个相什么的,也是莫大的骄傲。相片上的田媛是我的初中同学,她的梦想就是当女兵。女兵没当上,就一心想找个兵哥哥做男朋友,她那身军装,应该是军人情结的表现形式之一。后来我当兵去到部队之后,我俩开始鸿雁传书,我们恋爱了。可是我并没有给她军装呀,她那相片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影集之中呢?我没有丝毫印象了。不过,我们曾经相处的画面还是时常浮现在眼前——
我们老家属于浅丘地带,经济作物稀少不说,还远离大江大海大城市,所以比较贫穷,适龄儿童能读书者极少,当我背上书包上学的时候,都快10岁了。田媛比我大两岁,她上学的年龄更大。到初中时,我们都成大小伙、大姑娘了,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把她当成了心中的维纳斯。
那些年,我们家乡莫说水泥公路、高速公路,连一条像样的碎石路也没有,只有坑坑洼洼的泥泞小路。田媛是三大队的,我是一大队的,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我们家门口那条泥泞小路。那段路虽然不长,也不好走,但我们一同上学,小路就变得又宽又直又平顺了,一转眼就到了学校。我们几乎没有语言和目光交流,连手也没有碰过一次。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或者一前一后,或者一左一右,默默地走着,看上去像两个陌生人,但我们心中早就没有了距离。从春暖花开,走到霜雪遍地,一走就是两年多。
部队生活并非作家诗人想象的那么浪漫。它单调又枯燥,方块加直线,几乎是部队生活的全部。我的业余生活也不多,除了三五分钟训练,就是读书、写日记和给她写情书。为了写好情书,我去新华书店专门购买了《雪莱抒情诗选》《如何写情书》等书籍,还认真摘抄了《林海雪原》《安娜卡列尼娜》和《漂亮朋友》等一些小说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片段。
每天中午别人午休时,我就如饥似渴地阅读她的来信,然后心心念念地给她写回信。如果中午没时间,就晚上躲进被窝,摁亮电筒写。前前后后,不知道写完了多少本信笺,写秃了多少支笔尖。几乎天天都那样幸福着,快乐着,享受着。这也丰富着我的精神世界,激发着我的训练热情。
如果说后来我还能写点什么的话,应该是从写情书开始的,或者说是通过写情书磨砺出来的。我的军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与心中充满着蜜一般甜甜的爱不无关系。所以,我应该铭记和感谢那段经历。
全国恢复高考的前一年,田媛被推荐到西城上了大学,这本来是件好事,哪知福无双降。从她跨进大学门那一刻开始,我就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因为大学生与兵哥哥之间难以划上等号。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陡然间减少,由一天一封,减少到了一周一封。再往后,一月一封都不多见了,且原先那些滚烫的文字,也遭遇了寒冬,全部变得冷若冰霜。在最后一封书信中,她告诉我说:“有一位部队学员在疯狂地追我。”她没有继续往下说,但我心里明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她只不过遵循了自然规律而已。于是,痛苦中的我回了最后一封信,一封仅打了个句号的无字信。从那一刻开始,我在自己心中打了个坚定的感叹号。
次年,我到西城“集中考前复习”结束,准备离开西城的头一天晚上,她约我去她的租赁屋。当时的她应该喝了几杯,言语中透着浓浓酒气。她说她男朋友到外地实习去了,三个月之后才回去,很想念我,欲与我共进晚餐。我没有去,我担心那不是最后的晚餐。
真是鬼使神差。已经是一所高校学员的我,那年暑假回家路过县城时,在县招待所里居然与在那儿实习的田媛不期而遇。更蹊跷的是,我就住在她的隔壁。
再后来,她成了那位部队学员的妻子。我想,她那身军装,应该是她老公借的。她把那张相片送给我留作纪念,纪念她对军人的热爱,纪念我们曾经有过的那段洁白无瑕的过往。
我不怪她,因为她最终选择的还是军人。我也不恨她。若恨,我就不会把她的相片珍藏,并镶于影集扉页了。
(作者系重庆公安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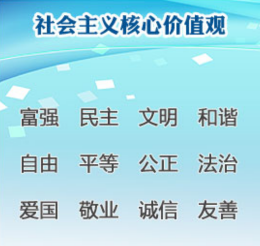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