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刁 竹
我一直试图将我生活过的小镇从细微处进行描摹一番。念头由来已久。其实,我在小镇生活的时间远远比不上我在城里的时间长,但童年留下的温暖与快乐,依旧如昨,以致于我偶尔也会午夜梦回。
从重庆市区上渝武高速,往合川宋代瓮城涞滩古镇方向车程约两个小时,就是生我养我的小镇了。
曾经,我对生我养我的小镇有点自卑,我不想对别人说出她的名字,因为她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字,小镇名称随时代变迁改了好几次,她也从来没有养出一个让人敬仰的名人。还有小镇离城到远不近的距离,也颇让人烦恼。说近吧,中间隔了嘉陵江、渠河,在高速公路通之前,得辗转公共汽车四五个小时,小镇的流行往往比城里过时好几年;说远吧,它没有因距离产生的神秘和美感,更没有我欣羡别人家乡的人杰地灵。尤其是我的青年时期,我羡慕那些从有历史名人、文化底蕴或者奇异景致的“大地方”出来的人,我认为他们比我天生就更胜一筹。
我的小镇,就是重庆郊区一个极其普通的农业小镇。小时候,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狭窄老街,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少女的我背着硕大的帆布书包,从街这头走到街尾的学校里,15岁那年,从街背后的公路走出了小镇……
街两边是低矮的青瓦房,从头连到尾,相邻两家墙壁共用。薄薄的板壁隔壁,可以偷听到邻居家里的对话。曾经有段时间,还是少女时,我睡在床上,常常从薄壁的缝隙望了过去,带着好奇和有点阴暗的心理,窥视隔离那位即将出嫁的姐姐,听她和她妹妹在屋里拌嘴,还有一些我渴望了解的生理知识;而我这边床上,我们三姐妹往往会因为抢夺被子而开始了脚踢脚的暗战,一床被褥,一个冬天就被我们踢得稀烂。于是,爸爸就请我们吃“斑竹笋子炒坐墩肉”,打得我们的屁股红一块紫一块的。
开了杂货店或者小吃店的街坊临街墙壁是一块块可以拆卸的木板镶成,用墨汁或者朱红油漆编了号。我家临街是青砖墙,修葺时爸爸在墙上嵌上一块爷爷留下来的雕花窗。只在我爸爸嘴里存在、我从未见过的爷爷听说是收废品的,家里很穷,但偶尔会收到点有意思的物件。我们就常常坐在雕花窗下的街檐下喝稀饭,喝出声音要遭我那当老师的爸爸呵斥。夏夜里,就在窗下铺块凉板歇凉。有的夏夜,有时也在街头围坐在一起,听食品站杀猪的那个老头讲评书,惊堂木一拍,我至今记着了他讲的摩登小姐找的那个对象:手一捞,金手表;脚一踢,华达呢;帽子一揭,半边白。
这个顺口溜,直到我进城里上大学后才明白其中含义。呵呵,说的就是一个年轻妹儿傍上一个有钱老男人。
上初中时,学了《天山景物记》,受新疆葡萄沟的启发,我那时有个理想就是当我们镇的镇长。我想,如果我是镇长,就可以要求小街每家每户在屋背后种上葡萄,对门适户把葡萄藤拉过屋顶,在小街上空纠缠,形成独一无二的葡萄小镇。这个想法是不是很棒啊?可惜我没当上镇长,也就没机会实施这个雄伟计划。
而今,我走出小镇已经30余年了。多年的城市生活,小镇已经不再让我刻骨铭心。年老的父母也早已随我们几个子女进到城里居住。只有老母亲,还时时在梦里回到小镇,她常常向我们描述她的梦:在乡下种田,在稻田里抓鱼,在街背后的碉楼前狂奔怕有鬼追来,在梦里看到我那已逝去多年的外婆——在我大学一年级的那个春节,我深爱的外婆因脑溢血的溘然长逝,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撕心裂肺的痛。
母亲还常常从老家人那里带回小镇的消息,虽然我们几乎每年春节都要举家回去一两天上坟扫墓,但那些消息仍然让我猝防不及,不知所措:这个某某死了,那个某某也死了……死者,或者是我们记忆深刻的老者,或者是父母辈的叔叔嬢嬢;或者是我父亲的学生,有时竟然我儿时的玩伴!这些年轻的逝者,有的比我长不了几岁,有的比我小,在意外事故中,在突如其来的病魔中,永远离去。
这样,因为这些消息,在纷繁而疲惫的城市生活之余,我也偶尔想起我的小镇……想起小镇的人们,我很想写写他们的故事,即使他们每一个都那么平凡,甚至有人被叫了一辈子小名或者外号,没有在街坊邻居中留下他们的“官名”。但他们,都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实,每让一个小镇的街坊邻居站在纸上,我的心就一阵悸痛,我的悲哀是只有远远望着他们受到命运的摆布。惟有在多年以后,当他们逐渐老去,或者荒冢长草了,我用寥寥数笔,记录他们不值得喧嚣的人生,让锦瑟年华里的人们在偶有点不快之时,还记得有一些小人物的辛酸作陪。
(作者系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资深媒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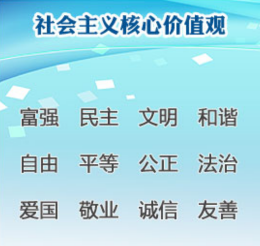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渝公网安备50011202500163号 